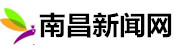本篇文章4967字,读完约12分钟
90年代初的夏天,我正要和蝴蝶去游泳。 我看到邮递员叔叔在我家信箱里装东西,我走过去打开信箱,看到x的大通知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通知书上说我顺利通过了。 专业是中文,性质是自费。 蝴蝶说了恭喜。 我说了恭喜你。 重新放进信封,用点力气放进裤子口袋,骑自行车,蝴蝶坐在我自行车的后座,和蝴蝶一起去x大旅行池游泳。 就这样,我顺利地通过了x大学。
我的高中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但日子还在继续,一点中断的意义也没有。 那个夏天当然发生了很多事件。 首先,父亲病了,没有得什么大病。 医生也说不出病因。 人整体消瘦,一周后父亲的病痊愈,出院了。 后来姐姐有很多新男朋友,又高又矮,又胖又瘦,足球队阵容十分雄厚。 姐姐在那次恋爱失败后,有了经验,严格来说阔种薄收敌人进入我退敌让我退缩的大致情况是,哪个臭男人每天围着姐姐转,让我家的旧电话机整天叽叽喳喳,搅拌我家让鸡狗平静下来,有时我真的是
终于进入了大学。 爸爸妈妈很高兴。 好像捡到了不小心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看我爸爸妈妈这么高兴的样子,是家里的大事。
王达也收到了西安交大的通知书,学的是法律。 叶如愿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学院,这一天我等了很久。 蝴蝶上了高三,她还在那个她认为可恨的学校呆了一年,这是没办法的事。 铁头光着身子出来了,我们很高兴。 那一年,街头剃光头很流行。 这是因为除了感觉凉爽之外,和不剃光头的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向大家提出建议。 大家已经很久没玩了。 请几天后去太白山好好疯狂一下。 大家一致赞同,只有铁头这几秒钟保持沉默,点头同意。
但是,铁头很快就食言了。 铁头不是轻易食言的人,但那天他食言了。
它傍晚热得像蒸笼一样,闷热,我躺在房间里,风扇吱吱作响,吹来的风很热,一点冷空气也没有,我想下大雨。 我望着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杂毛树孤独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只老母鸡正带领着小鸡群在树下觅食。
我又躺下了,心里有一种要发生的预感。 在这种时候,不发生任何事件是异常的。 果然,美好的天空,一瞬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雷鸣、轰鸣,生生震撼我,风雨交加,雨如石头,从半空中撞到头,猛烈地落在地上。 我爬起来,我再次看到那棵杂毛树,他在风雨中颤抖着身体,开心地叫着,那些鸡不见了,我想在大雨来临之前,他们安全地回家了。 地上的雨水很快变成了沙滩上的水坑,向低处突围,像蛇一样乱窜。
那时电话响了,我说体操,现在谁还打来? 我不耐烦地拿起电话,从那个头上传来了铁头低沉的声音。
铁头说:“西客,今天去。
我奇怪地问:“铁头要去哪里?
铁头说“南”。
我说:你要去哪里?
铁头说“海南”。
我说:“你去哪里做什么?
铁头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现在在哪里?
铁头说:车站。
“我来送行。 请等一下。
我没时间挂电话穿雨衣,所以出去,妈妈追,问她要去哪里,我没时间回答她,我没时间回答她。 雨打在我头上,然后往下流,除了感觉有点痛之外,感觉很爽。 我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向车站匆匆走去。 雨下得很大,打在窗玻璃上。 路上积满了水,车子好像在水里通过。 到了车站,车下来了,雨还很大,迎面打在我身上,我发现自己成了标准的水鬼。
我找到了西安出发去广州的候机室。 候车室人很多,但铁头很突出,在众多候车室的人群中,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铁头。 铁头上背着一个大背包,在人群中很显眼。 铁头和他的另一个哥们去了。 你叫什么赵大山? 他们在劳教所认识。 出来,彼此走几次,说一下自己的情况,总想拍拍腿,马上起来,和狗日的将来战斗。 经过几次商量,他们决定南下。 那个时候南方经济慢慢渐入佳境,形势大好,去南方淘金的人很多。
铁头要小心。 听说南方人很滑。 铁头说知道。 她说,为什么选择像今天这样的幽灵天气。 铁头咧嘴笑着说:“下午买的票,不知道晚上会不会下雨。”
开始检查票了。 派铁头上车。 我们乘着人流来到潮湿的站台,我用力敲击铁头的肩膀,说要小心。 铁头说没问题。 我让铁头人先上车,我把铁头大背包从窗户塞进去。 铁头探出头来,说我兄弟很珍惜。 铁头眼睛有点湿,不知道是雨还是泪。 铁头看了我一眼,说:“西客,那天喝酒,真的没带你的信封。 我知道,我差点忘了这件事。 铁头向我挥手,说再见,铁头进来了。 我站在潮湿的站台上,看着长长的列车慢慢地开动,慢慢地慢了下来,然后朝着黑色的夜晚方向前进,最终和夜色一起休息。
铁头的话还在耳边回响,我-真的-没有-你-没有-信-封---关于那个信封的事我差点忘了,它在某个特别的日子里勾起了我满满的心事。 真相无处不在,却被人为掩盖着。 我童年的历史被人为地抛弃在我的思维接触不到的地方,它以另一种隐藏的方式存在着,很久以来,风吹雨打,无人问津。
这样,铁头去了风雨之夜,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很久以前,西安市失去了铁头的影子,但西安市的日子还在继续,春夏秋冬,周而复始。 除了我之外,我的几个哥哥们都不知道,在风雨的夜晚,有个少年悄悄地离开了西安市,向遥远的陌生南方前进。 多年后回到西安城时,人们还记得铁头这个名字。 那时,铁头已经绕在腰上的有名的三花集团的总裁。 铁头怀念着那个风雨的夜晚。 那时西安城的很多高中请他做报告。 大学生们对他的成名史很感兴趣。 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对埃尔盖茨的故事感兴趣。
说起他的出世史,铁头总是抽出那风雨之夜,那风雨之夜留在铁头的生命中,不小心成为了铁头生命中最光辉的一页。 之后,铁头率领的三花集团转战南北。 我说起铁头,网民看起来像井冈山的故事,但实际上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党没有井冈山那段光辉的历史,人民群众可能还得在黑暗中摸索。 那时敌人还在城市里发疯。 没有那晚的南下,铁头就不会形成大气候。 在这个西部小镇,我听说了很多年后一夜暴富的神话。
送完铁头后,我回家,发现家里的灯很亮。 爸爸妈妈坐在客厅里,显然在等着我回来。 看他们的样子,在我回来之前,他们显然等了很久。 他们看到我回来了,松了一口气。 我咧着嘴笑了笑,走进了房间。 我想可怜天下父母的心! 如果可以选择,我将永远是别人的儿子。
我轻轻把门关上,顺便脱下衣服,扔在地上。
我想这一天终于结束了。
二十三
虽然感觉好像爱上了夏天,但夏天很快就会过去,明亮的颜色会留在我的人生中,之后谁也无法抹去。 夏天结束了,但记忆就像触角多的动物一样,一年四季都在疯狂。
夏天热,秋天凉爽,夏天过后是秋天。
在90年代初一个非常普通的秋天,我到达了x,正式成为了x大学生的一员。 x在西安城的高中有点名气,自由奔放的开放精神和稍微学习的大学不同,像中国的北大,充满了崇高的人文主义精神。 80年代末的夏天,我和铁头目睹了x大表情兴奋的学生们。 他们头上系着红布,流着眼泪,喊着反对xx的口号,坚定地走到校门外。
刘二的疯子也混在人群中,他脱下他的衬衫盖在头上。 刘二本很瘦,上半身裸体打一根骨头就露出来了。 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急忙来到人群面前,学生对他说了些什么,拽着他不让他去。 我想那个学生可能是她的孙子或者什么的,那个年轻人体面地看着他的奶奶,甩开她的手,跟着示威的人们走了。 我没见过早期革命党人的样子(在电影电视上见过),没见过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们是什么样子,但是那个夏天的记忆特别深刻,好像总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成为了关于x的大印象之一。
大学生活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我在镇上的小报社工作,写了一份有点长的文案。 我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 这个时候蝴蝶一般躺在床上做梦。 我花了大约五分钟刷牙洗脸,花了十分钟吃妈妈做的早饭,然后去上班。 8点整,我坐在报社的办公楼里,喝了一杯凉水,点了一包金丝猴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工作以来,我开始追踪到底是谁制造了“工作很美”的美丽谎言,但我一无所获。 说实话我讨厌上班,特别讨厌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我一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总是不守神。 发呆,拿着钢笔在白纸上乱画,最后把本来美丽的白纸都变了脸,支离破碎。 我很久以前突然发现这种行为其实是另一次谋杀。
这种无意识的破坏行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我想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得精神疾病。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绝对不是开玩笑。 我开始怀疑我的头开始坏了。 就像形状有点多又复杂的机器一样,有时一个两个零件坏了,一瞬间也找不到什么问题了。 但是,问题确实存在。 有时候我辛苦到想不起来刚想到的问题,我突然就忘了自己是谁。 当然,忘记了上大学的经历,我现在还不到30岁。 可怜的儿子还躺在蝴蝶的肚子里。
我不是一个好的诉说者,我的话总是背道而驰,前言不搭后语,缺乏说话者所需要的严密的理性。 在大学里,除了我们宿舍的兄弟们和我最好的朋友蝴蝶之外,没人怎么和我交往。 我认为这样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不善于表达自己。 我就像河里的河马一样,在剥下真正坚硬的外壳之前,谁也不知道我肚子里埋藏着闪耀的珍珠。
我不会说故事。 虽然我相信虚构是另一个真相。 因此,很难完美地复述上大学的历史,我个人也认为没有必要。 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在成长,同性恋、一夜性、艾滋病,还有五花八门的死法和生活方式等等。 人们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圈子里转圈,很少有人真正在意你的故事。 退一万步说,如果你真的对我的历史感兴趣,可以去人事部查我的文件,他们应该很容易处理。 烟酒不分家,有烟有酒,他都会拿出东东和你一起研究。 那上面的记录一定是这样开始的。
姓名:刘西客。
曾用名:空白。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陕西西安。
文化程度:大学本科。
等一下
毕业后,同学们已经作为鸟兽散了,有些人走远了,在寻找自己所谓的理想。 他们和我联系越来越少,只有少年时代的伙伴王达偶尔给我打电话,向我通报他在上海读研究生的生活。 因为我相信我在这个城市。 最终只剩下我了。 无论如何,在我的大学同学们完全没入脑海之前,他们一定会给西客留下一点印象。 这样想的时候,我没有主观的颜色。 我觉得别人和自己都必须那样做。 感谢上帝让我得到了这个真理。 把黑叫做白,把白叫做黑是不对的。 那把黑色说成灰也许不行,但画家似乎可以排除在外。 因为他们是色彩专家,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色彩,以色彩为主题跳舞。 在天才画家面前,你看到的颜色不再是真实的颜色。 但是像凡高一样用色专一,一心一意的画家已经死了,但是后来他在价值连城的画布上说:“我们是谁? 我们来自哪里? 你要去哪里? ”。 这样的句子,显然他疯了。 对天才疯子,我总是怀有足够的敬仰。 无论是凡高还是刘二。
说了那么多,接下来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西客在大学里绝对不是人物,但他显然在那个叫“6314”的宿舍里存在了4年,和“6314”密切相关。 这一定是。 他的历史和学校的历史,和人民群众的历史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 但是,有些人——至少“6314”的人应该知道。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客的历史也成为了他们历史的一部分,他们是相互补充的。 我说这话的时候,为了不被网友误会,特别是西客再次表明了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意思是见到西客的人可能记得他。 理由如下。
一、他逃课跑得很厉害。
二、他眼里总是出现没人的样子,很容易辩白。
三、以学校纪律为耳边风,以爱万岁为名与外校女同学一起文明行为,多次教育学校文明岗,其文明行为的真实照片多次在学校橱窗被曝光,但仍不悔改。
四、他在毕业前夕的世界杯期间,他兴奋地把点燃的床单从宿舍窗户掉了下来,在x大引起了巨大的火灾,被学校无情地分了出去。
我是西客,西客是我。 西客在x大的日子里,不长不短正好四年。 我上大学本来没有什么目的,但是如果爸爸妈妈不多次来我,我就不会在一个地方呆四年。 事实表明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即使进入社会也没什么用。 带红色记号的毕业证后来拿的作用就像身份证一样,告诉别人你有户口,你不是黑户。
我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说大学教育没有意义,相反,我觉得每个人都珍惜自己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学到的一点东西,无论是谋生还是为人民服务都可以。 我从小学开始就不是好学生。 我和哪个理想大的孩子不太一样。 当他们从小就打算自己成为科学家和文学家的时候,我和铁头们就开始了无限的学校。 我说的这些话是真的。 我已经是个傻孩子了。 如果你做得不好,只证明你比我笨。
(未完成)
标题:“真相(二十二”
地址:http://www.nxxlxh.com/nczx/179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