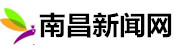本篇文章5946字,读完约15分钟
资料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她住在抗瘟疫的“异种”瑞典,但有黑色的皮肤。 她是穆斯林,不允许自己所属的团体成为疫情防控的弱势群体。
4月最后一天,傍晚7点,斯德哥尔摩街头。 夕阳的馀晖映在空旷的街道上,还没到晚上,已经是凉爽的习惯了,稀疏的人们匆匆走过,完全没有往年的热闹景象。
这天是从瑞典以前流传下来的节日沃尔珀吉斯之夜(也称为“春火节”)。 往年,黄昏到来时,各社区的居民聚集在一起点燃篝火,用歌声和火焰迎接春天的到来。 北欧的春天不像东亚那样温暖,在燃烧的篝火旁迎来脸颊和胸部燃烧的火焰,但背上必须感受北欧春天夜晚的寒冷。
一般来说,在结束这些庆祝活动后,政治活动家们还会参加第二天的五一节。 但是,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破坏了所有的庆祝活动,在被称为全球抗击疫情国家的“异类”瑞典,大部分公共活动也取消了。
一
幸好餐饮店没有被强制停止营业。 与艾玛的相遇定在4月30日---春火节下午4点,离市中心不远的咖啡馆。
阿马尔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大约1米8的头,浅黑色的皮肤,有点蓬松的长发,还有一些挑衅的痕迹。 她的视觉年龄也在20岁左右,不像大学毕业几年的27岁女孩。
艾玛有一头长发。 对自然缠绕的非洲裔来说,拥有直发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
她听说想喝点什么就礼貌地拒绝了。 “现在是斋月。 白天不能吃东西喝水”我有点不自然,对不起。 我知道她的穆斯林身份,以前在电话上的信息表达中她也提到斋月,我自然失礼了。 (年伊斯兰教斋月从4月25日到5月24日,期间从日出到日落不能吃饭和喝水)。
但是我在心里喃喃自语。 “你是虔诚的穆斯林,你为什么不戴围巾? 你的打扮也很世俗吧? 和我印象中的穆斯林女孩完全不同”。
除此之外,阿玛尔还有很多特别之处。
她是索马里裔的瑞典人,父母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但在瑞典出生长大。 她是四个大男孩的姐姐,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我是他们的老板”。 她的母语是瑞典语和索马里语,也会说流利的英语。
她是个虔诚的穆斯林。 她说她出生于虔诚的穆斯林家庭,长大后自然成为虔诚的穆斯林。 在公共场合,她不会用围巾包头发,也不会用长袍遮住身体的曲线和皮肤。 她穿得像普通的瑞典女孩,但这并不妨碍她内心的信仰。
她是警察局的文职人员,目前隶属欧盟的跨国项目“仇恨犯罪”(瑞典语: hatbrott——)是指通过比较对某特定社会群体的歧视或偏见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和联系的员工。
她也是网上索马里社区的活跃分子。 年下半年,她在ins建立了一个名为瑞典-索马里同学会( Swedish-somalialumniassociation )的在线社区。 这个社区现在已经成为社会交流媒体上最活跃的索马里裔瑞典人社区之一。 在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在瑞典突然发生的初期,她和社区的小伙伴们把关于瑞典语新型冠状病毒和个人防疫的视频翻译成索马里语,通过网络和手机在索马里社区宣传和传播防疫的相关信息。
二
瑞典自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爆发以来,在世界疫病对策国家中成为了“独特的风景线”。 瑞典不关闭边境,不停课,坚定地走着独特、符合自己国情的缓慢防疫之路。
但是“宽松”并不意味着所谓的“佛系”,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几个引起了很多误解。 因为瑞典的大部分公共卫生政策不是以“命令”的形式,而是以“提案”的形式提出的。 例如,维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性。 不让不必要的家庭旅行; 不要让70岁以上的人不必要地接触。 尽量在家工作。 怀疑有症状的家庭隔离等。
但是,除此之外,强制政策也在执行。 例如,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禁止访问幼儿园小学以外的学校。
简单来说,瑞典主张不能完全消除病毒,只能共存直到疫苗出现。 因此,我们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需要考虑“使很多人能够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承受”。 而且,有必要尽量延长时间,缓和疫情的扩散速度,抑制重症患者的增加曲线,降低医疗系统崩溃的风险,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急救治疗。 瑞典公共卫生局( Folkhlsomyndigheten ) 5月20日宣布,斯德哥尔摩20%以上的人相信有新型冠状病毒抗体。
阿马尔完全承认瑞典卫生局的防疫战略和具体的公共卫生政策,也信任政府。 但是,她对政府在疫情初期没有给予少数民族充分的关心和援助感到不快。
艾玛住在斯德哥尔摩市,斯德哥尔摩从疫情初期开始就是瑞典的严重灾区。 截至5月21日,瑞典新冠确诊病例达到31523例,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病例占1/3以上。
瑞典疫情开始的3月22日,斯德哥尔摩有9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其中6人是索马里人,这6人没有疫区和海外旅行的经验。
这个信息在瑞典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当时的媒体分解中,索马里裔居民很可能没有采取充分的防疫措施,很多索马里裔居民的瑞典语和英语水平有限,所以新闻信息的表达和传达有可能不顺利。 另外,在斯德哥尔摩的索马里社区,人口居住密度过大,生病时互相探望的习性也可能是提高感染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之一。
在网上,很多人把6名索马里人的死亡归咎于不掌握瑞典语,甚至有这样的声音。
“领取福利的人又少了一个。 哈哈! ”。
“我希望同样的事件发生得越来越多。 ”。
“今天最好的消息”
这些评论来自瑞典民主党( sverigedemokraterna )的facebook群“瑞典民主党和艾米的忠实朋友”,有16,000多名成员。 瑞典民主党是以反移民和反伊斯兰为第一政治纲领的右翼人民主义政党,现在是瑞典国会的第三党,埃米( per jimmie Åkesson )是现在党首的名字。
三
突然的疫情成为许多舆论将瑞典语相关信息翻译成索马里语的重要契机。
“最初,听说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蔓延,我感觉离我的生活很远。 但是很快在意大利,很多在意大利度假的瑞典人把病毒带回了瑞典。 接着在斯德哥尔摩,发现了养老院和一些索马里家庭发生的感染者。 之后,突然出现了死亡”。
“我们集体分享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各种信息,包括在广州的非洲人的遭遇。 但是看到斯德哥尔摩的索马里社区发生了聚集性感染,我想和另一个朋友在做什么? 我的朋友在视频制作企业工作,所以我们选择了视频。 我负责复印的翻译。 她负责技术事件。
翻译完成后,她们向ins和facebook发布视频,并将社区中的朋友转发给家人和朋友。 由于视频的翻译和分享,阿马尔受到了很多感谢和称赞。
“后来朋友说他们用手机给家人看了视频。 因为很多年长的家人平时不怎么使用社交媒体”。
但阿玛尔很快意识到,问题可能不是新闻不顺利。 索马里裔居民的瑞典语能力太差,不能马上接受和理解发生的事件的指责,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推测。
“意大利在2月中下旬开始爆发疫情,瑞典媒体也每天报道,但有很多滑雪、带新型冠状病毒的庭院。 3月瑞典国内开始流行后,有多少人在家去北部度假和滑雪? 他们对瑞典语的能力没有疑问,最初可以掌握政府和媒体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但他们依然越来越不关注这个问题,至少对行动没有任何表示”。
“喜欢旅行和度假的人把病毒带到瑞典,不是聚集性感染的索马里人,而是在全国的各种地方传播病毒。”
四
瑞典是欧盟最先进的数字经济之一。 根据瑞典网络基金会的数据,三分之二以上的瑞典人至少有一个时间段的在家网上工作。 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每天或每周在家工作。 高速宽带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很高,瑞典的社会和企业政策鼓励灵活的办公室和远程办公室。 这是瑞典人保持工作和生活平衡,保持性别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这种瘟疫来了,在家工作成为新的常态时,很多人对此没有表现出陌生和不舒服。
另一方面,瑞典50%以上的家庭只有一个成员。 这是欧洲所有国家中最高的比例。 在瑞典,高中毕业后年轻人会从父母家搬进来。 例如,在我妻子18岁生日那天,她父亲的贺词是“从今天开始,你是这个家庭最受欢迎的客人。 ”。
在南欧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严重的灾区,大人的孩子和父母住在一起更普遍。 乌普萨拉大学传染病学教授比尔恩·乌尔森( björn olsen )在bbc的采访中说:“如果你家住了好几代人,那当然会传得很快。 因为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等大城市的单身者很多,所以传达速度可能会有点下降。 ”。
阿马尔和她大部分同龄人一样,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公寓里。 这是30平方米以上的公寓,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和大厅,从地铁站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中央车站。
公寓所在的地区有个美丽的名字。 “盛夏节日花环”( midsommarkransen )是斯德哥尔摩最受欢迎的中产阶级社区之一。
另外,这里不是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的严重受灾地。
斯德哥尔摩新冠的严重灾区是很多移民(准确地说,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居住的地区。 比如斯德哥尔摩北部的厄尔巴( järva )地区。
厄尔巴地区的许多公寓里住着两代或三代。 因为在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大城市,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特别是对移民来说都要花费巨大的费用。 厄尔巴区高速宽互联网的普及度也很高,但对很多居民来说在家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
费尔泰马( fatima mohamed )是住在厄尔巴地区的索马里居民,在瑞典最大的报纸《dagens nyheter》的采访中,他说:“我听从了公共卫生局的所有建议。 但问题是,如果七口之家住在72平方米的公寓里,如何才能听从有关部门的建议呢? 如果家人中有人属于高危群体,情况会更糟。 事实上,即使你想保护,客观条件也是不允许的。 很多从事护士助理、家庭护士、公共汽车司机、商店员工、保姆等工作的人住在这里(厄尔巴)。 但是他们不能在家工作,不得不外出上班。 然后,病毒被他们带回家,在家里和会面中感染了父母。 ”。
疫情开始不久,斯德哥尔摩市实施了为老年人和高危人群提供疫情期间避难公寓的惠民政策。 但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政府不能提供免税的免费住房,因此每个公寓必须每月支付5000瑞典克朗。 但是,在埃尔巴地区,避难公寓到5月末为止有三分之二空着。 因为在很多有老年人的家庭里,这个价格还是太高了。
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 例如,根据法国民调机构的调查,56人住在六十平方的公寓家庭中,感染病毒的人数远远多于花园阳台的高收入家庭。 在纽约,感染率最高的五个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不足2.7万美元,比美国贫困线稍高感染率最低的五个地区的人均年收入超过11.8万美元。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英国贫困地区新冠的死亡人数是非贫困地区的两倍。
贫富差距、社会阶层间差距、移民社会融合等只有在日常严重讨论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在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的疾风如阵雨的催化剂下,迅速量化为对比明显的数据。 但是,这些数据所指的名称有点冷酷和残酷,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重症患者、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
五
面对疫情,艾玛没有太多不安和担心,每天坐20分钟的地铁去办公室。 但是,疫情爆发后,我没有去看望住在瑞典南部的父母,也没有和弟弟们见面。
为了避免战乱,阿马尔的父母于90年代初从索马里偷渡到瑞典。 现在艾玛的父亲是公共汽车司机,母亲做家务。
住在瑞典的索马里第一代移民由于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大多位于瑞典社会的中下层,从事蓝领和服务领域的工作。 当然,除了索马里,来自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第一代移民都有同样的遭遇,在移居国家长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经济弱势群体、文化语言弱势群体和社会资源弱势群体。
但是,和很多海外中国移民一样,阿马尔的父母也相信教育的重要性。 他们的五个孩子都接受(或接受)大学教育(瑞典高中和大学教育是免费的)。 这可能看起来很正常,但实际上,在瑞典25~34岁的人口中,接受过大学4年以上教育的人在同龄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为35%。
到了移民的第二代,文化上、语言上的弱者地位几乎没有了。 瑞典长期奉行社会民主,国民贫富差距小,瑞典社会阶级观念非常薄弱,移民二代从小就可以获得平均和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这确实像阿玛尔一样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的两代移民粗略地提高了自己的阶层,比父母们得到更多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
瘟疫打乱了阿玛尔的许多日常生活,但并没有打乱她的精神生活。 她从4月25日开始一个月的封斋,从日出到日落不吃。 工作日下班回家后也遵守礼拜的工作。 逊尼派穆斯林每天祈祷五次。 祈祷前,阿马尔穿上长袍戴上围巾,仔细检查浴室镜子前围巾是否遮住了所有的头发。
但在办公室工作期间,阿马尔通常不做礼拜。 那里没有特别的祈祷室。 另外,每次穿长袍和围巾都有点麻烦。 这也是她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小妥协。 艾玛说,除了祈祷,包裹全身的长袍和围巾不是穆斯林女性的必需品,信仰是越来越多的衷心选择。
阿马尔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瑞典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度过的。 她的父母是虔诚的穆斯林。 每周五,阿马尔的父亲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去附近的清真寺,阿马尔和她的母亲在家祈祷。 虽然小镇上的穆斯林不多,但她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过种族和文化上的歧视,她的好朋友也很多是当地的女孩。
后来,她主修政治学去了另一个城市上大学。 因为她对各种公共议题和集团结社很有趣。 这也是她在ins和facebook上成立网络社区的理由之一。 这个以索马里裔的“移二代”为中心的社区有相似的民族认可和文化背景。 每周都有新的代理群主管理社区,大家入住和共享照片,有时比较各种热点话题展开讨论,类似于活跃的微信群,但社区开放度接近微博。
阿玛尔至今单身,她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手。 对此,她没有具体的量化要求,我只是希望将来的一半也是穆斯林。 在索马里,我知道大部分同龄人已经成为父母。 索马里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0.4岁( 2006年,世界银行)。 其中,阿马尔更接近瑞典同龄人,瑞典女性有世界上最晚的平均结婚年龄,33.8岁(,世界银行)。
社会对男女平等权的高度接受度无疑是女性晚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意味着像阿马尔这样的女性可以拥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社会空间,寻找和构筑自己的亲密关系,计划未来职业的迅速发展。
艾玛现在是政府公务员,可以说体面稳定,但她希望取得突破。 现在的事业项目结束后,我打算离开瑞典,在某个国际机构和组织里工作。
但是,至少现在阿马尔非常关注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下的索马里裔社区的境遇。 她们和什么样的同志社区伙伴们利用她们的语言能力和专业信息为她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关心和支持”的同胞们发声。
除此之外,阿玛尔也期待斋月结束的开斋节的到来。
“我真的很想和父母和弟弟们一起庆祝开斋节,但不知道今年可以不可以回去。 我真的很想吃妈妈做的菜,她把食谱和方法都告诉了我,但我知道那真的不一样”。
图片来源:摄影/武玉江
标题:【要闻】疫情中的黑色肌肤
地址:http://www.nxxlxh.com/nczx/15082.html